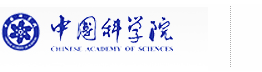郝晓光的背后,挂着那幅大名鼎鼎的竖版世界地图。张小叶摄

该图为新的南半球版世界地图,已于今年9月由湖南地图出版社出版。图中的地形地貌采用全数字化高程数据计算生成,不掺杂人为的描绘成分。

传统的横版世界地图

新的北半球版世界地图(为方便对比,此图横置) 根据北半球版世界地图,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2002年9月开通了北京经北极直飞纽约的航线,这是北京飞纽约同类航线中最短的一条,比穿越太平洋的直线距离缩短了8000公里,单程飞行比跨越太平洋的传统航线减少了3个多小时。
地图均由郝晓光提供
原定2014年元月正式出版的《竖版世界地势图》,像新生的婴儿一样迫不及待地于今年9月间提前问世了。这实在是因为“她”在腹中孕育的时间太久了:从2002年在湖北武汉编制完成至今,地图的作者郝晓光等待这一刻已经11年了。
尽管竖版世界地图早已在相关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但获得这张“准生证”,使它得以与世人正式面见,却一路坎坷。难怪郝晓光用让旁人听来有几分夸张的比喻说:“就像双目失明的哥白尼,在临终前抚摸着散发墨香的《天体运行论》说:‘我推动了地球’。”
把世界地图竖起来。在改革创新、转型升级的今天,我们更需要这样的创新意识。当记者结束采访,走出位于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时,不由得想:我们生活中还有多少习以为常的“横版世界地图”也可以竖起来?
400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着一张世界地图来到中国,在那张地图上,中国被置于整个世界的极东一角,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那以前,国人以为“世界唯中国独大,余皆小,且野蛮”,中国是天下的中心,而外国人散布在遥远的岛上。后来,出于传教考虑,利玛窦将投影方式作了改变,将中国置于地图中央。这就是第一张中文版世界地图,直到现在,我们从中学教科书上的地图看到的世界依然如此。
横版世界地图的缺陷显而易见。要使球形的地球变成平面,必须利用投影技术,这就必然会带来变形:在传统的世界地图上,这种变形使南极大陆的面积扩大了好几倍,南极点被拉成了一条线。而郝晓光的竖版世界地图中,地球被沿着两条纬线“切开”了,“仿佛一颗人造卫星,从太平洋上空永恒不变的观察点上,飞到了南极和北极的上空,向下俯瞰到了新的世界”。
在“南半球世界地图上”,南极洲仿佛一只正在开屏的白色孔雀;在“北半球世界地图上”,许多国家的距离被拉近了,原本在世界边缘的北冰洋,则成了被各国环绕的“地中海”。它们与以亚洲和欧洲为中心的横版世界地图放在一起,使人们得以完整地观察世界。
德国地球物理学家魏格纳因在地图上发现了两块大陆边缘形状的吻合之处,后来创立了“大陆漂移说”;郝晓光也怀有这样的希望:有一天人们能够通过这张竖版世界地图获得灵感,像哥白尼或者魏格纳那样“推动地球”。
艰难的出生记
在竖版地图诞生时,郝晓光就面对着一堵无形的高墙,有关部门甚至组织了地图界的权威人士写文章批判,认为这种尝试是“故弄玄虚,对地图科学的无知”。
郝晓光说自己就像个“相声演员”:“下面的听众都听着我‘抖包袱’——讲竖版地图的美和意义,感觉很新鲜,哈哈地笑,但这个包袱我已经说了一遍又一遍,早就腻了。”
这个有趣的说法,却是竖版地图艰难出生记的写照。2002年,竖版世界地图编制完成后,郝晓光就面对着一堵无形的高墙。在竖版地图诞生时,有关部门甚至组织了地图界的权威人士写文章批判,认为这种尝试是“故弄玄虚,对地图科学的无知”。
阻力来自何方也显而易见,“我国体制内有那么多人从事地图的测绘、设计和制作,怎么可能由一个非地图设计制作部门的人来制作一张新的世界地图呢?”
事实上,郝晓光本人并非地图的业余爱好者。他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1977年考入同济大学测量系,学历至博士、博士后,毕业后即进入中科院武汉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对于他主编的竖版世界地图,著名地理专栏作家、《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主编单之蔷评价极高:“其精良考究的程度,甚至超出了我国正式出版的地图。”
然而,当批判雪片般飞来时,郝晓光却很兴奋:“压力一旦大到一定程度,就不称其为压力,反而被转换成一种巨大的机会。”此后数年,他花费数十万,数百次前往北京,一一拜访曾经撰文批判过自己的权威专家。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和单之蔷结成了莫逆之交。郝晓光把它归结于自己“抖包袱”的能力:“除了地图,我还能聊好多别的话题,天文地理、人情世故、哲学历史…单之蔷每次见到我来了,就把我拉进房间,闭门谢客。然后咱们能海聊六七个小时,连厕所都舍不得上。”
在单之蔷的叙述中,他们的情谊是这样结下的:“多年来,我总在办公室附近碰到郝晓光,他提着一个黑色的旅行箱,连姿势都是一模一样。每次他见到我总说:‘怎么样?神了吧,不会扑空。’但办公室并不是我长待的地方,出差、外出开会、躲到咖啡店里写东西……直到有一天他说了实话:‘我来北京,如果事先给你打电话约时间,你是大忙人,我能见到你吗?扑空和见到你的比例是20∶1吧,见其他人也是如此。’为了世界地图的出版,他至少来北京500次了。”
后来,单之蔷成为了郝晓光的“贵人”之一,这位极有声望的“地理界才子”,被郝晓光的韧性和坚持所打动,多次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撰文推荐竖版世界地图。其他人也是如此,当年批评过新地图的权威,在郝晓光一次又一次地拜访和游说下,几乎都“倒戈”成了新地图的“拥趸”。郝晓光说,竖版地图11年后终获出版,是“众望所归”。
“一般特别好的东西都会遭人恨,我不但不遭人恨,还得到了许多‘恨的反面’。”他笑道,“为什么?因为这么好的地图不能出版,还被批评、被打压,这使得大家都同情你、支持你。反过来,要是一开始就顺风顺水的,占了许多便宜,现在谁待见你?”
竖版地图之美
“看地球仪,你只能准确把握世界,却不能完整把握世界;地图是一种人文的创造,它让你可以一下把世界全部控制住。”
郝晓光今年55岁,他的父亲郝孚逸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郝晓光的童年是在“复旦大院”(即复旦教职工小区)里度过的,他10多岁就读遍了世界名著,高中毕业后,郝晓光主动报名下乡,一点儿都不觉得环境艰苦,还写起了小说:“许多知识青年都喊苦喊累,但我却特高兴,还尝试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一种有文化的氛围。”
他反问:“为什么梁晓声要写《今夜有暴风雪》?因为憋不住。那时,我们知青和老乡间的感情特别好,感情好就心情好,心情好就要搞创作。这是憋不住的事情。”
在那个年纪,郝晓光精力充沛、兴趣广泛,选择将测量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似乎有着极大的偶然。1977年恢复高考后,有个复旦中文系的老师看到了郝晓光写的小说,想把他招入中文系,还请他父亲来游说,结果,“老爷子过来一问,才知道我已经被同济大学测量系录取了”。
对地图测绘的兴趣,源自郝晓光的高中毕业实习。那年,学校将三个毕业班分为测绘、铸造和化工三大组,郝晓光所在的班级恰好被分入了测绘组。
讲到这段故事时,他铺开一张纸,顺手讲解起测绘地图的基本原理:“首先,你选定一个建筑作为测量对象,将测量仪器置于一处,开始测量仪器与建筑的距离和角度。再将它按照比例尺缩小后,标绘到图纸上,这就是测绘。”
在那次毕业实习中,郝晓光亲手绘出了人生中第一幅地图,这种看似简单枯燥的基础测绘工作却让他着迷不已:“卫星定位伟不伟大?天宫对接伟不伟大?但这些伟大的背后,就是这些基础测绘工作组成的。”
在郝晓光看来,测绘的伟大意义甚至远远超越了它的实际应用。尽管投身自然科学30余年,但少时的人文教育却滋养了他的思想,科学和哲学之美被统一起来了,竖版世界地图就是两者交汇后流淌而出的产物。
多年后,郝晓光带着自己绘成的世界地图,向世人宣布地图是“科学和人文的交融”,因为地图是人们头脑中的世界:“有了地球仪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有地图?因为地球仪表现的是真,而地图表现的是美。看地球仪,你只能准确把握世界,却不能完整把握世界;地图是一种人文的创造,它让你可以一下把世界全部控制住。这个就是真与美、准确与完整,使用与想象。”
追求真理的幸福
“当你走进真理,只觉得巨浪扑面而来;当你远离真理,又看到星辰闪闪发光。”
郝晓光更喜欢称自己是“哲学家”。
拿编制竖版地图这件事来说,“横版地图上南极变形那么大,为什么没有人去关注?这是哲学问题。所以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是顺着逻辑和观念自然流淌而出的”。
竖版世界地图正式出版前,已经在航空航天、科学考察、军事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应用。但郝晓光却觉得,在“哲学家的头脑”里,世间万物中,唯有思想本身是值得一提的:“当我在编绘地图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它的实际应用。我一直在想,中国人勤劳勇敢、吃苦耐劳,但想象力稍微差一点,创新稍微少一点。竖版世界地图最重要的启示,是为中国人插上想象力的翅膀,学着换一种视角看世界。”
所以,“当地图绘制出来后,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么美的一件作品”。
这样的想法使他精神充实,总是身处平静和幸福之中。郝晓光的同事朋友,把他这种天然的“乐天”称为“郝式哲学”:“在任何境遇下,他都高高兴兴的,从来不倒苦水,还能把周围的人逗乐。”
为什么从不忧愁?郝晓光说,因为自己“从不考虑简单的事”。“我是个科学家,我追求的是哲学上、逻辑上最高的美,哪有空管那些蝇营狗苟、使人烦恼的小事。”
与地图本身相比,为出版地图所做的十多年来踏破铁鞋的努力,在郝晓光心中也成了“不值得一提”的小事:“谈不上吃了多大的苦,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而且,世界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定理,当你特别冲动地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怎么都做不成。后来,坚持久了,心里慢慢腻了,这件事反而水到渠成了”。
在郝晓光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大名鼎鼎的竖版世界地图,书橱里摆满哲学书籍,橱顶放着他的自行车头盔,书桌上摆着他自制的台历,上面印有他引以为豪的“诗配照”——他喜欢旅游和摄影,出国参加个会议,会把自己的折叠自行车也托运过去,一得空闲,就到处骑着玩。拍下满意的照片后也会“诗兴大发”写上几句,他把这种自创的艺术表现形式称为“诗配照”。
这就是郝晓光的日常生活,55岁的他依然像年轻时一样,保持着对这个世界旺盛的好奇心。“我只做想做之事,因此总是轻松愉快。”他说,“要是给我一笔项目经费,规定我去制作地图,我肯定心里急死了,根本搞不出来。一流的工作都是神来之笔。”
但他并不想让竖版世界地图成为自己一生的里程碑,充满能量的郝晓光,在人生已过半百之际,依然雄心勃勃地计划做更多的事情:绘地图、写诗、研究马克思哲学和萨特戏剧……在“想做之事”的长长清单中,有些出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有些则是为了享受追求真理的纯粹乐趣。
他这样形容真理之美:“任何物质的力量都无法与真理的力量相比……真理是永恒的,不受时间的摧残;真理是绝对的,不受谬误的歪曲。当你走进真理,只觉得巨浪扑面而来;当你远离真理,又看到星辰闪闪发光。”
新地图期待中国魏格纳
郝晓光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摆着一个可能会被载入地图史的地球仪。它被郝晓光从支架上拆卸了下来,以便思索把玩。由于年代已久,球体已经蒙上了一层细灰,有些褪色,上面还有设计时留下的点点记号。
1569年,荷兰制图学家墨卡托以“墨卡托投影法”为基础绘制了第一张世界地图:地球被沿着一条经线竖切开来,海洋和陆地的形状投影到平面上后,就成了通行世界数百年的横版世界地图。目前国际通用的世界地图基本是两个版本:亚太版和欧美版。亚太版以太平洋为中心,东经150度为中央经线、西经30度为左边经线和右边经线。欧美版则以大西洋为中心,以0经度为中央经线、西经180度为左边经线、东经180度为右边经线。
但在郝晓光的想象中,地球就像一个苹果,有无数种切法,他还想寻找到更多富有美感且具有实用价值的切线。
这条设想中的切线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尽量不切割陆地,二是保证时区的完整性。对于后者,由于一个时区跨越15度,因此必须以整15度为单位进行切割。
他最终将新切线从无数种切割法中找了出来,不多不少,正好两条。在北半球世界地图上,他沿着南纬60度纬线把地球切割开来,而在南半球世界地图上,这条切线是北纬15度。按照这种切割法画出来的两幅世界地图,完全不切割陆地,尤其是北纬15度,它在南北美洲之间的最狭窄处穿过中美洲,完整无缺地保留了南北美洲大陆的形貌。
“仿佛是神来之笔。好像地球就在等待这一天,等待人们从这样的角度来欣赏它。”《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主编单之蔷这样评价。
若像郝晓光那样将地球比喻为苹果,我们以常规的方法竖切它,看到的果心近似一只“蝴蝶”,但如果横切的话,就会发现一个“五角星”。新地图不仅在直观上具有革命性,也是一场认识和思维的革命:薄薄的地图反映的是人头脑中的世界,它曾经推动过人们扬帆远航,探索新世界。然而,如果将这种视角固化和唯一化,它呈现的美丽与宏伟就可能束缚人们的思维,僵化人们的头脑,仿佛世界就仅仅是这幅地图表现的那个样子。
“两张新地图不是颠覆,而是补充。”郝晓光说,“将四张地图放在一起,可以发现,它们每一张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去观察世界,也有其特殊的应用。如果把四张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了一种理想的世界图景。”
除了形式和逻辑上的美感,竖版世界地图的实用价值也很快得以体现:2009年开展的第26次南极科考中,在传统地图上表现雪龙号的航线示意图时,因投影关系产生了视觉偏差:南极洲变形严重,长城站、中山站的距离被大大拉伸,原本环南极洲航行的轨迹,也因变形呈现出“8”字形,并将南极洲“排斥”在外。
而在郝晓光的南半球版世界地图上,这些视觉偏差被避免了,雪龙号经过的关键港口依次沿着航线分布,长城站与中山站的地理位置清晰明确。因此,早在2004年,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就以南半球版世界地图为指示图,开展了中国第21次南极科考远洋航行。
北半球版世界地图首先被运用于民航领域,由于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陆地和五分之四的国家都位于北半球,因而北冰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地中海”,它也拥有联系亚、欧、美三大洲的最短航线。但在传统的世界地图上,北极地区是被“切断”的,无法在上面标注航线,郝晓光的世界地图却解决了这个问题。据于此,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2002年9月开通了北京经北极直飞纽约的航线,这是北京飞纽约同类航线中最短的一条,比穿越太平洋的直线距离缩短了8000公里,单程飞行比跨越太平洋的传统航线减少了3个多小时。
北半球版世界地图还在国家重大战略问题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传统地图的世界观中,总以为如果真的有他国的导弹袭来,大多是穿越太平洋而来的;但北半球世界地图上则显示出北极被多国包围的客观现实。如果真有导弹从美洲袭来,应该是从北极上空来,因为距离最近。”郝晓光说,2006年,他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北扩问题”专家研讨会上提出了这个观点。这个提议最终修正了北斗卫星的覆盖范围:按照原计划,这一范围在中国的北部终止于国界,在东部则伸入太平洋——如今已由太平洋指向了北极。
但郝晓光还期待着这两张地图能够推动更多的东西。1910年,德国地球物理学家魏格纳在观察世界地图时,产生了对大西洋两岸吻合的直觉印象,并创立了大陆漂移学说。“就像苹果掉到牛顿头上,他就想出了万有引力那样,魏格纳的发现是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郝晓光说,“但为什么大陆漂移说不是在东方产生的呢?因为我们没能面对一张能激发灵感的世界地图,中国常用的是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亚太版世界地图,大西洋东西的两块大陆分处地图的两端。”他希望,中国的魏格纳,有一天能够面对新版的世界地图,找到那把“真理的钥匙”。
在利玛窦带来第一张框架基本正确的世界地图之前,中国并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念和一张好的世界地图——这或许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没能用它去环球航行的原因之一。在郝晓光看来,好的世界地图,能够培养出好的世界观念,催生出探索世界的美好愿望。这也是他奔走十多年,执著地推动地图出版的原因:“要让它走进寻常百姓家,带给人们多元的、崭新的世界观念。”
(原载于《文汇报》 2013-12-10 09版)